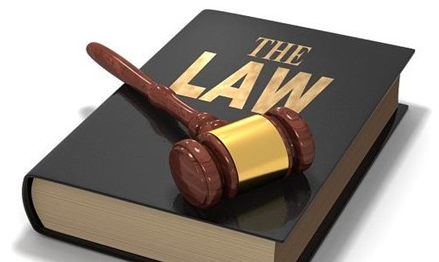
在一个法治社会,法律具有必要的权威性、稳定性、统一性,不得被挑战或违反,而尊重、维护和遵守法律,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义务,通常情况下任何个人或团体不可能获得随意对抗或违反法律的权利。在各国实践中,只有少数案例表明,以不服从行为、违法行为抗议类似于种族歧视这样的被社会多数公认的恶法,才能在事后被以“公民抗命、违法达义”的名目豁免于刑事处罚。公民抗命实属法律实施中的个别例外,远未能形成一般司法实践,很难说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法律概念,未可轻易确定为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,否则整个法律大厦就难免有倾覆之虞。
对公民抗命行为正当性的认定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,因为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违法者行为动机的正当性、合理性,必须有严格的限制条件,要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。实践中违法者所持的违法理由往往有较多的主观色彩,能否成立,始终存在争议,而法庭对其理由的审定也难免排除非法律因素的干扰。如果在审理过程中过于强调违法者的主观意愿,并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,难免导致法律公平正义的失衡,造成法制的不稳定和社会混乱,损害或动摇现有法律的权威性、统一性和稳定性。
有人认为言论自由、表达自由构成公民抗命的权利基础,把二者混为一谈,甚至视公民抗命为某种宪法权利,这一说法恐怕很难成立。言论自由、表达自由是一项受国内法和国际法保障的基本人权,有确定内涵,可以普遍适用;而公民抗命属于极少数例外,实践中不一致、法理上也存有争议,远未构成一种普遍人权,不可与言论自由相提并论、混淆起来。况且言论自由并非可以肆意妄为、无法无天,而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,不得超越或违反法律。规定言论自由的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19条第三款明确指出,该等权利的行使负有特别责任及义务,需要有特定法律予以限制,包括必须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,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、公共卫生或风化等。倘若将公民抗命说成是言论自由,其意图既想为公民抗命的违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,也会使言论自由蒙上了肆意违法的不良形象,很难认为是一种严肃的法治精神。
2014年发生于香港的“占中”行动被人们标榜为一起公民抗命的案例,虽然其非法集结、涉及暴力的违法性已被社会多数及司法机构所确认,但仍有人强调其动机和意愿的正当性与合理性,并以此来掩盖其违法性质,博取社会同情。那么“占中”的动机和指向是什么呢?众所周知,“占中”的直接目标是对抗和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普选的“8·31决定”。 在这里,“占中”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,直接挑战其宪制地位,否认其不容置疑的职权及决定的法律效力,从而将自己置于同宪法相对抗的地位,因为正是国家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。其次,“占中”所反对的“8·31决定”的内容,完全是依据香港基本法第45条做出的,其正当性、合法性均来自于基本法。反“8·31决定”其实就是反基本法第45条,在这里,“占中”者又将自己置于同香港宪制性法律相对抗的地位。那么难道规定香港普选的基本法第45条是一个恶法吗,这样一种由极个别人主张的主观判断能够成立吗?如果这一判断不能成立,那么“占中”的正当性、合理性又表现在哪里?显然,在这里应当受到质疑的不是“8·31决定”和基本法,而是自诩为“公民抗命”的“占中”行动本身的正当性。
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实施必须以法律为保障,保证法律公平正义的适用则是维护法治的必要措施。维护香港法治,不仅仅要依靠香港本地法律,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。宪法和基本法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,居于香港法律的最上端,是整个香港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依法治港,首先就要体现出宪法、基本法的宪制地位和作用,唯此才能真正保障“一国两制”全面准确的实施。
(饶戈平,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)
《 人民日报海外版 》( 2018年02月14日 第 04 版)
原题:“公民抗命”辨析
责编:刘思悦